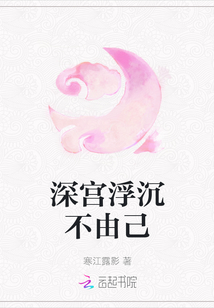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歲月荏苒,大燕王朝——史書上自是不存——已安然度過數(shù)十個春秋。然而,“安然”只是一種勉為其難的說法,因為北方的瓦狄部落,不時南下騷擾。他們當下駐扎的土地,原本屬于另一個國度,另一個王朝,這王朝與大燕是兄弟之邦,兩相交好,互不干涉。某年,瓦狄部落長驅直入,侵占這一王朝,殺國君,占皇宮,隨即揮師南下,企圖一舉奪取大燕。大燕朝廷不能坐視不管,經過一堆繁雜的博弈,皇帝親征,大軍北上。這是大燕絕大多數(shù)百姓所了解的。如果把懷思城城樓上的守軍算在“百姓”之中,也未嘗不可。
與大燕其它城樓一樣,即使在正月十六之夜,這座城樓上,也有人忠心耿耿地守護。夜班對他們,已是家常便飯,可他們仍無法擺脫疲憊。整座城沉浸在無邊的黑夜里,站高處俯瞰,竟能看不見一星燈火。該睡的人都沉睡,不該睡的人面對黑暗,總會因單調而生無聊,因無聊而生倦意。
好在“十五的月亮十六圓”,這天無雨,夜空中的一輪圓月,當然是明亮的、可愛的。士兵們若是不安,若是焦躁,看看它打發(fā)時間,總比無所事事好。聊天如何?似乎可以,不過要是違反軍紀,自有懲罰可消受。
現(xiàn)在,士兵們緊張地監(jiān)察周遭人等,時不時抬頭望一眼月亮,思念不在身邊的親人。有的不止會思念親人,還會思念親征遠方的那個皇帝。他會安全嗎?說出征瓦狄就出征瓦狄,敵人會把他怎么樣呢?打仗可不能鬧著玩,死在那兒回不來,就要改朝換代,改朝換代了,新人又怎樣?……
“有人在嗎?”城墻下一聲叫喊,打斷了好幾位士兵的思緒。他們一個個不自覺慌亂起來,但馬上又恢復軍人應有的鎮(zhèn)靜,沖聲音發(fā)出的方向聚集,探頭探腦。其中一位用粗糲的大嗓門吼道:“你是誰?”
“我是當今皇上身邊的使者,要送陛下親筆信回京師,現(xiàn)在城門已經關閉,我去不了啊。”下面那位回答。他的說話聲被喘氣聲裹著,時重時輕、時急時緩。守城士兵明白,他跋涉已久。
“城門不能開,這有根繩子,我放它下來,你爬上去吧。”那位問話的士兵喊道。使者聽見,心內有底,稍稍安靜。沒過多久,一根繩子從城墻上垂下,正好垂到使者身邊。他立馬握緊繩子,嫻熟地手腳并用攀登城墻,不一會兒就爬上去,被守城士兵們團團圍住。
“各位大哥,在下真是皇上的使者,你們趕快派個人去京師吧,越快越好,送宮里面去——”他從隨身包袱中掏出一卷布,把它塞入離他最近的兵士手里。這兵士不是別人,正是之前沖他喊話的那位。幾個守城的湊近身子,想問他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可他剛松手,就倒地不省人事。
軍士們皆半信半疑。手持“來信”的那位,發(fā)愣片刻,又思考一會兒,最后決定,派人把它送到京師,是真是假,皇室自有說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邊上幾個人,他們都點頭同意。于是,大家連忙派出一位精力充沛的衛(wèi)兵,跨馬送信入京師。
昏迷的人,被他們中的兩位抬入不遠的士兵營房,擱在張簡陋的床鋪上休息。一個時辰后,他醒來,發(fā)覺自己身邊站著位軍士,正忙于給他倒水。軍士見他醒了,趕忙伸手遞水,又問他究竟怎么回事。他略帶慌亂,呷口水,低聲說,皇上在邊關大敗,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信是皇上親筆所寫,得送到京師太后那里,上報軍情。軍士大駭,不自覺搖動送信人肩膀,問他皇帝是否受傷,傷情是重是輕,如今人在何處。說完,他意識到自己嗓門大了點,合攏嘴。送信人說:
“皇上不見了……”剛說完,他便被一陣突如其來的困意擊倒,倒下睡去。軍士“倏”的一下站起身,既不去倒水,也不去守夜,而是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轉悠,嘴里念念有詞:“皇上有難?不會吧?他頭腦這么不清楚,沒準全是胡言亂語呢……可要是皇帝有難,一家老小該怎么辦……要不要走”。整晚,他焦頭爛額,竟意外地沒被周公喚去。
比他更焦頭爛額的,是皇宮里的李太后。她坐在寢宮里,被一堆宮女太監(jiān)圍著。一位宮女從慌慌張張的送信人手里接過信,佯裝鎮(zhèn)定,把信遞到李太后手中。李太后是當今皇上之母,皇帝出宮在外,她雖不能干政,可宮內外人人都當她是皇帝生母,過問些天下事,無甚不妥。她攤開信,緊盯布上的文字,杏目圓睜,表情凝重,兩手微微顫抖。送信的人跪在太后身前,低首彎腰,宮女只能看見他的發(fā)髻。這時,他的表情比太后還要凝重。不止凝重,他還多一分驚恐,誰知會遇上什么?
信上寫道:“遠征大敗,朕已被俘。瓦狄人索要金帛,逼朕速求。”字不多,卻嚇住了太后。起初,她不相信是兒子寫的,細觀良久,沒錯,這確是他的字跡,她從小就看到的,一筆一劃,絲毫不差。她怔住。
她知道一些宮外的人不情不楚的事情。出師之前,兒子畏首畏尾,不肯出兵。她聽聞此事,羞愧萬分,下朝后叫他過來,二話沒說,將他劈頭蓋臉地斥責一通。他涕泗滂沱,第二天上朝,就昭告群臣,自己不但會派兵,還會親征,不僅要親征,還要帶上親信宦官黃正。“有黃先生在,朕絕不會敗給小小的瓦狄。”他坐在龍椅上笑鬧道。幾個大臣苦苦相勸,皇上充耳不聞。最后,兵部尚書長跪不起,請求隨從皇帝征伐。皇帝酸澀一笑,說:“好,好。”
如今,敗報已至,徒呼奈何。她又細看信中每一個字,“索要金帛”,要不要送些金帛給他們?不送點錢去,兒子怕是要不回來了。可要真送,送多少?倉庫里財寶有的是,瓦狄人沒見過的還有一堆,送肯定不是問題。對,不如就送,先把消息封住,再把金銀財寶送走,換他回來……昨天還在宮里慶賀中秋,歡聲笑語,今天怎么就橫遭不測?
她下定決心。“你先退下。”太后扭頭對送信人說。
送信人喏喏連聲。“是,是”,他口中不斷稱是,兩腳抖動著后退兩步,轉身離開太后寢宮。他剛走,太后就把宮女一齊叫出:“你們聽著,皇上出征戰(zhàn)敗,已經被俘。你們去倉庫搜些金銀珠寶、古玩字畫,多拿些值錢的東西裝好,我會命人把它們送瓦狄那邊,想法子把皇上討回來。你們快點,別耽誤時辰!”最后那句,她拉長了音調,叫得宮女心里發(fā)毛,手抖的手抖,腿發(fā)軟的腿發(fā)軟。
“哦。”宮女們齊齊應聲,快步跑出。跑得快的,差點把跑得慢的人撞倒。“等一下!”太后跟在她們后面嚷嚷。宮女們回頭望著太后,一個個臉上掛著不合時宜的木訥感。李太后來句:“動靜別太大,別傳到宮外。”宮女們又像之前那樣,慌慌張張跑向倉庫。李太后不放心,頭既不抬也不轉,命旁邊兩個宦官進庫房監(jiān)督,別出亂子。
宦官走了。宮女也走了。李太后倚在一根柱子上,默念道:“皇帝,從我把你抱養(yǎng)來的那天起,你就是我兒子。不管怎樣,我得把你救出來,好歹我們也相依為命那么多年……”她微微抬頭,半癡半傻地凝視一根木柱,又默念道:“要不是你,我也坐不到太后之位!”
宮女們手提麻袋,在架子前奔波,手忙腳亂地把倉庫里有些價值的什物向里扔。金條、首飾、古董、畫卷,一個接著一個被丟入袋子,它們互相撞擊,“噼噼啪啪”聲此起彼伏。聲音不大,但她們每個人都以為,這聲音劃拉了她們的耳膜,讓她們倍感不適。一位宮女失手把耳環(huán)掉在地上,她蹲下去撿。邊上的另一位宮女退后一步,踩住她的手指。被踩中的宮女正在專心致志地拾耳環(huán),沒料到一只腳會踏下來,不禁尖叫。踩她手的宮女,驚愕地看她一眼,立馬把腳松開。“耳環(huán)碎了沒?”她問。
“沒有,你看,還好……”她強笑回答,用淤青的手指鉗起耳環(huán),慢慢塞進麻袋。剛問話的宮女回過頭,一聲不吭,若無其事地挑揀東西。
各類什物裝了幾十個麻袋。宮女宦官一同走出倉庫,見李太后不知何時已經站在外面。她的后面,還立著一群馬夫,和八輛馬車。出倉庫的宮女里,有幾個面露不悅之色。她們是被其他宮女拉去搭把手的,不知根底,但看李太后的神情,知道不對勁。
李太后顧不上她們,比比劃劃地指揮:“把這些家伙都放馬車上,小心點,別碰壞了!”話音剛落,宮女宦官就把麻袋一個接一個摞在馬車里。宮女手提,宦官肩扛。有個身形瘦小的宮女,提不動大袋子,只能拖行。剛拖到馬車門旁邊,她便倒地不起,雙腿蜷縮。一個宮女和一個宦官上前扶起她,拉她到附近坐下休息。李太后時而命令這邊,時而指使那邊,見到有點松懈的,會不自覺罵幾句。
八輛馬車頃刻間滿滿當當。李太后讓宮女宦官退下,他們有的應幾聲,有的沉默,都老老實實走開。太后見他們遠去,向一干馬夫使個眼色。之前,太后已經向他們告知全部因由,他們知根知底,也向太后遞來同樣的眼色。
太后頷首,側身,沖宦官厲聲道:“剛皇上遞信給我,說他身陷瓦狄敵營,要我們送些金銀財寶去贖他。剛才你們也看到了,我搜羅了這些什物,就是為了把皇帝換出來。你們現(xiàn)在就跟這些馬夫一同上路,盡快到瓦狄人大營里,告訴他,我們已帶這些財寶給他們,叫他們把皇帝放回來!”幾個宦官聽出她的聲音有些怪異,既發(fā)抖又有些嘶啞,底氣不夠。他們二話沒說,走上前,加入到不大不小的贖人隊伍中。
他們走在前面,太后緊緊跟在后面。他們離開皇宮,門緩緩合緊,太后豎在原地,不言不語,雙目鎖住宮門。“我派人去救你了,”她默想,“你一定要平安回來!”她慢慢走回寢宮,腦海中又盤旋著一個想法:“不要讓太多人知道……”她撇過頭,望著偏殿所在的方向,想:“比如他……”
第二天上午,偏殿里已有不少大臣。他們大多年過五十,蓄上或花白或烏黑的胡須,戴上大同小異的烏紗帽,身穿顏色一致,只是花色不同的團領衫,遠遠望去,某些人或許不能區(qū)分他們誰是誰。他們中,有的人氣定神閑,有的人心煩意亂,有的人驚悸莫名。
外面一位宦官高聲曰:“英王駕到!”
剛才還神態(tài)各異的眾位大臣,此刻齊刷刷地換個臉色,鎮(zhèn)定自若。他們站起身,迎接這位“英王”的到來。
一位身穿親王服的青年走進來。他不過二十歲,但神色之間已有一絲貴氣。這種貴氣,在如今的皇親國戚中,已屬難得。他眼神清澈,但清澈中有幾分威嚴,又有幾分凌厲。大臣們看見這對雙眼,有的會慶幸朝廷出了一個好親王,有的會憂慮自己撞上一個狠角色。不過更多的大臣還是困惑,皇上整天和黃正胡混,“先生”來“先生”去,可以讓“黃先生”坐在他們上邊,還能一時興起,帶黃正闖蕩沙場。現(xiàn)在進來的這人,年紀尚輕,此前少在宮中活動,他懂什么?
青年走近偏殿上座,安靜地坐下。大臣跪地叩拜。青年依禮回復:“眾卿家平身!”大臣們紛紛站起,回座位。
這位青年不是別人,正是當朝皇帝蘇中成的弟弟,英王蘇中鈺。蘇中成北征,帶離很多朝中重臣,命他在京留守。他起初猶豫不決,萬般推辭。畢竟,他自幼住在宮外,進宮見父親、見兄長、見李太后,也不過逢年過節(jié)那幾次。成年后,他大多時間住在英王府,平日不過讀書、談天、狩獵。他最常做的,就是和英王府講官們議論國事。論起黃正專權,他憤憤不平,卻不知如何是好。朝中許多大臣,他留守前同他們素不相識,也不清楚如何管理。但他不好拒絕,只能答應。每日白天進皇宮偏殿,與太監(jiān)議論國事,議論完,回英王府歇息。
如今,他已在這里居守近一月。他意識到,自己在英王府里所學的那些知識,在這里似乎都能派上用場。同大臣們論政,與在英王府中同講官談天,似乎別無二致,只是這些大臣們地位更高,在他面前更加嚴肅。他表面迎合,實則內心別扭。身前的這些“團領衫”,他既把他們當臣子,也把他們當朋友。他希望自己有很多摯友,甚至可以有更多。
當然,親王的威嚴,他不能放下。他清清嗓子,掃視一眼群臣,故作嚴肅地問:“眾位愛卿,皇兄北征,至今未歸。請問各位有何見解,不妨一提。”說完,他的表情又恢復輕松。
下面一人起身云:“侍講徐世銘有事啟奏。”蘇中鈺很熟悉徐世銘此人,他平日話雖多,但大都是些陰陽五行之術,用兵之道談的不多。大臣們對此,或頂禮膜拜,或嗤之以鼻。蘇中鈺對他的話,向來姑妄聽之,就禮貌地問:“你有何高見?”
徐世銘高談闊論:“臣夜觀天象,覺必有不祥之事發(fā)生。殿下應作長計,免后顧之憂。”
他剛說完,四周就響起一陣輕輕的嗤笑聲。蘇中鈺想笑,不得不低下頭憋住。等情緒稍微平復,他問:“是何長計?”周圍的笑聲頓時止住。
“陛下,”徐世銘道:“臣以為瓦狄虜了皇上,必會出兵南下,威逼京師。京師居于北地,離瓦狄太近,風水不佳。不如遷都金陵,以高枕無憂!”
不知怎的,蘇中鈺聽到這話,隱約感覺別扭。徐世銘話音剛落,有人喊句“此言差矣”,說話者是兵部侍郎胡尚謙,他邊說,邊站起身,出班前行。他又義正辭嚴:“徐君只知天文術算,不知人事。戰(zhàn)場情況瞬息萬變,豈是你那套讖緯之說能預測清楚的?”他又對蘇中鈺說:“求殿下萬不可聽此人之言!”
英王會心一笑。比之徐世銘,他更欣賞胡尚謙的才華和人品。他話音輕快:“胡侍郎所言即是。徐世銘,你的讖緯之術,一會兒準一會兒不準,滿朝文武都不知該不該信。你還是多鉆研正道吧!”說完,他又對胡尚謙回一個微笑。胡尚謙微笑頷首而坐。徐世銘也回位,順帶偷偷白了胡尚謙一眼。胡尚謙、蘇中鈺,乃至在坐其他大臣,都沒發(fā)現(xiàn)。他們繼續(xù)談國事,談民生。
早朝結束。蘇中鈺回府,眾臣回家。回府路上,他決意去噦鸞宮探望生母吳氏。
來到那里,吳氏對視著兒子的雙眼,先是喜悅,后是關切。她說:“你現(xiàn)在留守京師,國事眾多,無需時常看我。身體要緊……”她說不下去,只是盯著兒子。
“母親不用這樣。我很好,有眾位大臣支持,可施展拳腳。太后這些日子很少插手,平常也不過問我們什么——”提到“太后”二字,蘇中鈺眉頭微皺。他話鋒一轉:“娘,她對你怎樣?沒欺負你嗎?”
吳氏微微低頭,慘笑,不一會兒神色又變得木然。她吞吞吐吐:“我不是一直都很好嗎?你每次來看我都問這句,我都聽膩了。”她垂下眼皮,一言不發(fā)。
蘇中鈺眼睛紅了。他帶著哭腔:“您老是這樣說,從我小時候起就這樣說……”說完,他抱著母親脖子,啜泣。
吳氏推開他,問:“云兒呢?”
“他整天就是跟著芷兒和奶媽學說話,學識字,再過一年,就該讀書了。”
“蘭蘭呢?”
他笑逐顏開:“她和芷兒玩得很好,常隨她學女工,學認字,字認得不錯,刺繡就老是歪歪斜斜,前幾天還戳破了手指,逼得芷兒天天自責……”
吳氏輕咳一聲,表情肅穆。蘇中鈺見母親如此,一愣一愣,住上嘴。吳氏扁一扁嘴,壓低聲音:“我勸你不要老同唐姑娘混在一起。她和我一樣,原來就是個侍女,兩年都生不出孩子,又沒什么家教,你何必天天纏著?之前我看你子嗣不豐,勸你臨幸個多產的女子,好為朱家開枝散葉,你找我說的做,孩子不就有了嗎?還是要以后代為重。”
蘇中鈺心痛如絞。他愛母親,也同情她,可她這番話令他如坐針氈。他怕聽到“后代”這兩字。他想不通,這兩字在皇家,為何如此招人牽掛。他只是輕輕“嗯”一聲。
二人又寒暄許久,還一起用膳。吳氏送蘇中鈺出宮,李太后站在她的寢宮門邊,斜睨這對母子。蘇中鈺不知她在身后,起駕回府。
一路上,他坐在馬車里想心事,從社稷,到唐姑娘,再到后代,東想西想,他雙手垂在腿邊,如同身側的車廂簾一樣。如果他能掀起簾子看看街道,他或許會大吃一驚,因為他能發(fā)現(xiàn),街上已多出不少傷兵。他們有的倒伏在客棧門前,有的踉蹌地走在街上,有的勉力和過路人聊天。此時燕軍戰(zhàn)敗的消息,已傳遍大街小巷。轎里的蘇中鈺,對此自是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