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大腦檢測失敗了。
監測室外的辦公區域內,好幾個同時啟動的液晶屏幕都在各自按部就班地工作,發出“滋滋”的電流聲。
毫無波瀾地劃掉檢測表單上的一個序號,線條精準又利落,趙峰自在此工作的十多年來,重復相同的動作,周而復始,一直如此。
象征性的三下敲門聲過后,監測室的門被推開了。
“趙哥,你方便看一下我的報告嗎?”
是隔壁從其他研究所的維檢部門挖過來的高級檢修員,剛接手了上一任晉升留下的六號室。
“小周?你急嗎?”
“不急不急,你抽時間時候看下就行了。趙哥,你袖口臟了哦。”
“放桌上吧。”點點頭,撣掉了袖口上的粉屑,掃了一眼對方的著裝,“打算下班了?”
“嗯,陪女朋友過紀念日,約在七點。”有些不好意地摩挲了下之間的戒指。
“現在都六點一刻了,趕緊走,約會不能遲到。”
“成,先走了,趙哥明天見。”
“嗯,明天見。”
重新面向監測室,透過防護玻璃,趙峰看見剛剛被判定銷毀的大腦自動傳送上了一條長長的傳送帶。
傳送帶盡頭通向的是猙獰的欲望與貪婪,透明黏膩的培養液附著地表與渾濁破碎的腦渣融為一體。
曾經,他也親眼見證過銷毀的過程。
調閱出傳送帶上大腦的資料:編號A561,腦齡41年,檢測結果是擁有過于充分的自我意識與創想力及豐富成熟的專業知識,不符合重置條件,啟動重置失敗,進入強制銷毀。
簡單粗略地掃了幾眼,趙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文檔上的的字跡慢慢變淡變淺,如同夢貘蠶食夢境,歸于空白不留痕跡。
腕表上的短針介于八九之間,當日的工作進行到收尾階段,重新檢查了監測室里放置的培養皿和數據反饋的接線,確保無誤后脫下身上的制服掛回了鐵質衣柜。
同樣一起隱藏在陰影滋生的角落的是還帶有余溫的胸牌,上面寫著:拯救者研發中心維檢部九號室資深檢修專家趙峰。
走出研究所后門,趙峰撥通了妻子的電話。
“老婆,我已經在回來的路上了。”
“……那我給你準備宵夜,沒什么事,先掛了,你路上小心。”
“嗯。”
貫穿凜冬的寒風,氣勢浩大地被用力摩擦后發出了“嗚嗚”的女人嗚咽聲,平地乍起的警笛向世人哀嚎出了最后的喪鐘。
研究所西南方向第三個路口的深巷里,發現了一具男性遺體,遺體周圍散落了許多被碾碎的黑百合的花瓣,警察抵達后快速封鎖現場,拉起了警戒線。
死者是一名男性,表情猙獰的臉上呈現青紫腫脹且眼球向外突出,皮膚出血點的特征,沒有明顯的打斗掙扎的痕跡,但是被害人衣服凌亂,身上多處擦傷,頸部有明顯的勒溝,法醫出示的初步判斷的死因是勒斃,出現明顯的死后僵硬現象,而死者的大腦不翼而飛了。
通過沿途監控,捕捉到了被害人最后出現過的地點,Au Revoir餐廳以及附近的研究所。
坐在客廳的趙峰喝下第一口熱湯時,上門了解情況的警察將其帶回了偵訊室。
“姓名?”
“趙峰。”
“你和被害人是什么關系?”
“關系不錯的同事。”
“研究所的監控顯示,被害人在六點十五分左右曾經去找過你,你們說了些什么?”
“他把寫完的報告交給我,請我幫忙看一下而已。不過交談的過程中有提到,他七點的時候和女朋友有個約會。”
“根據路邊監控拍攝的影像,結合法醫解剖后給出的死亡時間,大約是在七點四十五到八點半之間,這段時間里你在哪里,又做了些什么?”
“在研究所加班,途中有打電話給小周關于報告的事情,他七點半回來過研究所,沒多久他就離開了。然后我是大概九點半才離開,當時還給妻子打過一通電話,我想研究所的監控能夠證明我說的話。”
“最后一個問題,經過了解,無論是你的妻子還是被害人的女朋友都聲稱你們是在公司上班辦公職員,但明明你們都是任職于業內頗有名望的研究所,為什么?”
“警官。沒有人會告訴別人,自己受雇于一個屠宰場,是個沾染了淋漓鮮血的劊子手的。”
趙峰被一個人留在了偵訊室里,深藍色的墻體將他團團包圍,不可避免地聯想到了把所有一切都可以吞噬的蒼藍大海也是如此地冷靜幽深,試圖強行激發潛藏在他心底的不安與惶恐。
偵訊室旁邊的會議室里負責偵訊的警員們交換雙方取得的情報,一個胡子拉碴左耳上別著香煙的中年男人率先把手上的筆錄拍在會議桌上,大刀闊斧地拉開椅子坐下。
“周紹強的女朋友說,與被害人分別后就直接約了閨蜜看電影去了,直到被我們找來偵訊前都一直在一起活動。”
“她有說與被害人分別的時間嗎?”
“說是七點半左右,被一通電話叫出去的,離開得很匆忙。”
“有說是誰嗎?”
“她說她也不知道,聽被害人的語氣非常禮貌也很恭敬,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他們分別以后,他的女朋友再也聯系不到他了。”
“和法醫那邊的驗尸報告上的死亡時間對上了,你們那邊有什么收獲嗎?”
擦掉鏡片上霧氣的身材有些偏瘦的警員翻閱著剛剛從趙峰那里錄取的口供,字斟句酌地訴說紙上的內容。
“這么說來,這兩個人都沒有犯案嫌疑了?”
“如果確認了他們口供上的內容屬實的話,的確如此。所以,到時候也不能硬是把他們留在偵訊室里了。”
時間的針腳分秒不停地割裂過去與現在,距離案發三十又四個小時被判定出局,刑偵大隊成員依舊忙碌在自己的崗位上,爭分奪秒地抓出蛛絲馬跡。
不知道已經重復多少次倒退快轉,以秒為單位的停格畫面,情報搜集的搜查員還在捕捉案發當日周紹強消失在監控前的影像畫面。
“真是太奇怪了,每次都是走到第二個路口,人一眨眼就不見。”伏案在顯示器前的搜查員用食指指向了監控里被定格的一個畫面:周紹強走在人行道里側,非常貼近沿路商店,甚至差點就離開了監控的邊緣。下一秒,人就消失了。
謎團與真相之間差的是一幀的距離。
身后的會議桌上以及白板上到處都散落橫七豎八的案件資料,與案件相關的照片,在場的所有人都嗅出了空氣中的緊張感。
“老張!有進展了!”
昏暗的審訊室內,一束強光射穿了一室的陰暗與污穢,坐在犯罪嫌疑人特席上,被光束打到臉的趙峰像偵訊時那樣沉靜地目視前方,等待最后的臨終審判。
老張將兩張照片出示在趙峰面前,是研究所監控室所拍攝到的畫面:一張是趙峰在監測室內身著制服的樣子,左上角的監控時間是18:35,另一張同樣是在監測室內工作的畫面,只不過時間顯示的是19:35,多出了周紹強的身影。
“你有沒有想說的?”
“之前在錄入口供的時候我有說明過原因,只是因為報告需要修改才把小周叫回來的。”
又舉起了兩張明顯是同一畫面,但是局部放大的照片;“現在能看出區別了嗎?”
審訊室內的一切都被凝結了,撲通,撲通,一下,一下,在場的三個人幾乎似乎都聞不可見地聽到對方有規律的心臟跳動。
“你不回答可以。我來告訴你,這兩張照片有什么區別。”
“左邊這一張是你案發當天在監測室工作的畫面,由于監控的拍攝角度的原因,可以看見畫面上你左邊制服的口袋并沒有放置任何東西。”
“而到了19:35的這個畫面,周紹強進門的同時,你左邊的口袋突然憑空出現了一個沒有完全塞進口袋透明的小角。”
“那是你的工作牌吧。”
“在工作牌出現之前,并沒有記錄下你有任何將物品塞入口袋的舉動,你能解釋一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嗎?”
趙峰的的視線釘在了照片上,左手大拇指無意識磋磨食指指尖,接受了下一波的炮火攻擊。
“唯一的解釋就是,你,篡改了監控視頻,想要隱瞞背后的實情。”
從手邊抽出一張來電記錄的拉錄單,拍在了照片上,雪白色的紙張在強燈光下變得刺目。
“周紹強曾經接到過你的電話,并且在通話記錄上也確實有你的名字,他的女朋友也能證明。”
“但是,問題在于你打了幾通電話。”老張點了點單子上的號碼,在周紹強死前的一個小時里,直接到過三個電話,卻只顯示了兩個號碼:周紹強的女朋友和趙峰。
“當女朋友的面接到電話是你在19:15撥出的,從餐廳回到研究所只需要15~20分鐘的時間,與所有周紹強出現過的畫面所吻合。”
“可是,你又在19:25的時候再一次撥通了他的電話。”
“周紹強的手機來電記錄里并沒有這則通話,說明被人為刪去了。”
“而且,他之所以會在街上的監控里突然消失是因為……”
“我改了見面地點。”
趙峰打斷了對方的話,再次開口沙啞的聲音在密閉的審訊室回蕩,每字每句吐露的都是被踩在砂礫中粘附的粗糙感。
“為了送他更好地上路。”魔鬼露出了堅硬的獠牙,雙目赤紅地嗤笑嘲諷。
被揭穿后,趙峰的身體一下子就放松了,半倚靠在座位上:“那個蠢貨,還在電話里一口一個趙哥地問我該怎么走呢,他肯定不知道自己那么積極找的路,居然是通往地獄的。”神情癲狂而扭曲。
“他消失去了哪里。”
“進商店從后門穿出去,右拐走個幾百米就到巷子里了,那里可是一個監控都沒有。”
“你為什么殺他。”
“他該死!”
“他殺了我的兒子。”趙峰的話完美契合了老張手上的個人經歷:趙平,六歲,意外車禍,經搶救無效死亡,肇事者周紹強。
“可那起事故是一場意外。”
“沒錯,我知道是一場意外,但我無法原諒的是他在車禍發生后做的事!”
“他做了什么?”
趙峰扭曲的表情像是按下了停止鍵,一下子歸于了平靜,冷笑:“他偷走了我兒子的大腦。”
“他串通了搶救的醫生,把我正在與死亡做搏斗的兒子的大腦活生生地取了出來!”
“然后對外宣稱搶救失敗,憑借自己是腦部檢測師的身份把我兒子的大腦帶回了研究所。”
老張一下子想通了其中的關節,表面上是通過正規渠道以腦部研究的名義進行試驗和檢測,實則是以灰色渠道以活體取官的方式,培育編輯的瘋狂試驗。
“你們是在犯罪!”另一個審訊員拍案而起。
“后來你是怎么發現的?”資料的下一張就是關于拯救者研究所的相關明細與備案。
“工作調動的原因,我進入了現在的研究所,直到在去年的交流會上他的研究報告的內容非常精彩,當時我們所長就希望能夠招攬到他,是我審查他的個人資料和研究成果的。”
“我發現了,他早期的論文研究課題所使用的研究對象的數據資料和身份背景與我兒子一模一樣。”
“在一次醉酒后,他全部都說出來了。”
“所以,策劃一切為你兒子報仇,還留下了黑百合。”
“是。”
被鮮血吞噬鑄就的黑色百合,永不超生的詛咒。
滴滴滴——,發生警報——
滴滴滴——,發生警報——
“編號A561腦波異常波動10秒。”
“生物腦集成運行正常。”
“記憶儲存區發出高頻次信號。”
“腦陣計算機運行正常”
“切斷信號通道。”
“無法檢測體征。”
“重置失敗。”
“啟動強制銷毀。”
“再重復一次,編號A561,啟動強制銷毀。”
監測室透明玻璃的另一側,檢測師站在屏幕前校對完顯示的資料后,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周紹強。
周而復始,千錘百煉。
文檔上逐漸清淺的字跡依稀可見:
編號A561,腦齡41年,原名趙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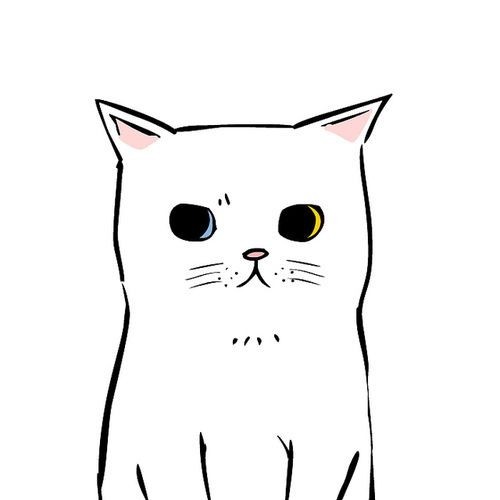
山澗河
上述研究相關的內容不可考究,只為自己的腦洞。
